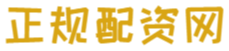
发布日期:2025-02-10 21:44 点击次数: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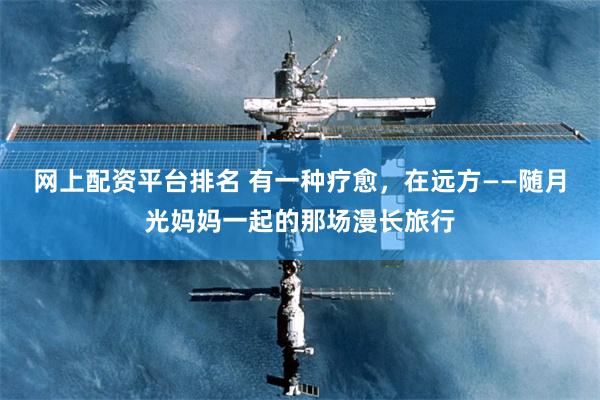
几年前网上配资平台排名,我随杭州一家电视台去宁夏采访。采访结束后,我们去了赫赫有名的西夏王陵。
王陵位于银川市西,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保存最为完好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专家学者认定的最重要的西夏文化遗址。
本来我对那些远古的帝王陵墓和遥远的西夏文化并无太大的探究欲望,但一位有地方志学术背景的陪同告诉我们:历史上蒙古灭亡西夏时,相传有一批皇亲国戚后宫嫔妃,从遥远的西夏都城,一路向西南逃亡,越过川西高原、岷江大峡谷和大渡河,最后流落到彼时人烟稀少的四川丹巴。那是隐藏在横断山脉中的一片秘境,荒无人烟的深山冷坳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了蒙古人的追杀;秀山丽水的清澈澄明洗去了逃亡者身上的污垢,抚慰了他们惶惶不安的心。从此,这些西夏王朝的皇亲国戚和后宫嫔妃就留在了丹巴。丹巴历史上是东女国的故地,本来就有女性王国的遗风流韵。西夏王朝皇亲国戚后宫嫔妃的到来,又将其美丽贵气的血质注入了这一方土地。血脉交融,一代代人传承着祖先的美貌和气质,这才有了今天的丹巴美人谷。
展开剩余94%丹巴草坡上的羊群让我看到了“母羊的心”
这位陪同的介绍,让我深感意外。因为从2011年开始,我一直在追踪采访一位从杭州到丹巴美人谷的核桃坪援建希望小学,被当地人称为“月光妈妈”的女教师。我先后三入川藏,走遍了美人谷的山山水水,寻找那些被月光妈妈资助的孩子们,挖掘那些因为家境贫寒而濒临辍学,又被月光妈妈的爱呼唤回来,重进校园的藏地少年身上发生的故事。
月光妈妈和希望小学的孩子们
与西夏王陵的此番初识,让我对一位东部西子湖畔的母亲远赴西部丹巴教育扶贫的寻访,似乎有了一种历史背景的观照。
那段时间我正应《收获》杂志之约,准备采写一个教育话题的专栏“燃灯者”,月光投身其中的对西部的教育扶贫事业,能否为国家东西部教育的协作和融合探索出一条路径,是我寻访中最希望深入了解的。
这一寻访就是十四年,十四年漫长而艰辛的寻访经历,一路伴随着温暖,终于在2024年岁末之时,成为一本名叫《月光妈妈》的书。书中写了十几个藏地孩子在月光妈妈的关爱和引领下成长的故事,也道出了教育扶贫,扶的不仅仅是“贫”,更多扶的是“志”。
《月光妈妈》 袁敏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书出版后,反响竟超出我的预想。我原以为,书写一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带领一群爱心人士关注教育、为边地藏区奉献大爱的故事,在常人眼里可能会有歌功颂德之嫌,在这个人人都活得不太容易的当下,读者对此也许会疏离,或敬而远之。没想到许多人看了书以后纷纷反馈很感动,更有不少人表示希望加入月光妈妈的公益团队,也想为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脱贫的藏地孩子送去更多的温暖。
回望十四年的寻访写作之路,曾经有过无数个温暖的瞬间。这些瞬间,有的来自月光妈妈们,有的来自孩子们;这些瞬间,像天上飘来的云一样雪白而和煦,它们无疑在彼此疗愈的同时,也温暖了我。
一 木桶里的那朵云
《月光妈妈》书写的故事中,第一个被《文学报》转载的是《永远的四年级》。
故事中的女孩名叫噢措,是一个让人心疼得掉泪的小女孩,家住在海拔3000多米高山上的牧业村。别人家的孩子七岁上学,噢措却不行。奶奶瘫痪在床;爸爸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伤及腿神经,干不了重活;一家人生活全靠妈妈放牧支撑,一去放牧就走得很远,一走就是两三个月;两个弟弟还年幼。她小小年纪,顾老又顾小,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去很远的地方用木桶拎水回家……
有张照片是月光和另一位爱心人士皮皮2012年去牧业村家访时,在村里的学前教育学校前给孩子们拍下的。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两间土砖房,一间做教室,一间做老师的办公室。教室内光线昏暗,窗户没有玻璃,只是把塑料布蒙在窗框上遮风挡雨。教室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木渣,只是为了隔断地下渗出的寒气,让孩子们的脚不要太冷。
由青海省政府改造后的直亥村希望小学
但就是这样的学习环境,孩子们的脸上依然充满明朗的笑容。这些笑容温暖了月光,抚慰了她在现实生活中被戳得伤痕累累的心。但照片中没有噢措,即便是这样一所小学校,噢措也去不了。
月光和皮皮往回走的时候,在一处歪斜的木房子前看到了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的手里拎着一个大木桶,里面装满了水。小女孩仰起头,看着月光和皮皮,脸上露出灿烂的笑。
月光向小女孩招手,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啦?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小女孩没有回答,依旧看着月光和皮皮一个劲儿地笑。看得出来,小女孩其实很想回应月光,但因为听不懂汉语,纵然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次不经意的邂逅,却在小女孩的心中种下了要上学的种子,她要学汉语,想听懂山外来的阿姨说话,也想和她们说话,问问山外面能看到什么?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就是噢措。
月光第一次见到噢措,当时七岁
月光和皮皮给噢措家留下了三千元钱,让噢措父亲一定要让女儿上学。月光当场就要认领噢措结对,但被皮皮抢过去了。皮皮说,你已经结对那么多孩子了,噢措由我来资助。
村里的老支书得知消息赶过来,说村里还有几家很困难的孩子。月光和皮皮一一了解情况后又认领了三男五女八个孩子。
也许是提着一木桶水却笑得很灿烂的噢措太让人心酸了,月光和皮皮都没有意识到,她们心中的天平不知不觉中就倾向了牧业村的女孩子。
2015年,牧业村报上来的资助名单中,噢措的年级写的是四年级。月光很高兴,噢措终于读完初小要上高小了。2016年丹巴资助学生名单报上来的时候,月光又看到了噢措的名字,但表格上显示,噢措仍然在读四年级。2017年,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噢措的年级一栏里,依旧写着:四年级。
月光很诧异,但那段时间她被其他事牵扯精力,分身乏术,而我对生活中出现的疑窦总是充满探究的心理,无论如何也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2022年秋天,当我决定重返丹巴,再次采访那些被月光妈妈资助的孩子之时,我第一个想采访的就是噢措。
屈指算来,噢措应该17岁了,正常情况下,她应该读高中了。可是,当我们向牧业村的老支书了解时,老支书的回答依然是:噢措在读四年级。
《永远的四年级》篇名就是这样来的,背后的心酸让许多读者唏嘘不已,而我提笔写这个故事时也是潸然泪下。
其实,我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噢措。
2022年去采访丹巴孩子们时,正是疫情发生之际。噢措其时已经离开牧业村,去到离家很远的炉霍卡娘乡降达小学上学,年已17却还在这所学校读四年级的噢措,因为疫情封校,没能接受我的采访。我通过老师用微信视频连线上她时,手机镜头里的她汉语表达非常费劲,从头至尾说的话不会超过十个字。
无奈之下,我只好列出了七八个问题,发给她的老师,请老师指导她回答我的问题。
一天以后,噢措的书面回答来了,表达的流畅和清晰令我吃惊。我问老师,是噢措自己写的吗?老师说是。
书出版以后,出版社派出一支纪录片拍摄小分队,奔赴丹巴和直亥两地拍摄每个孩子当下的生活影像。我请出版社的同志将噢措的视频素材发给我,我想在没有任何剪辑的情况下捕捉噢措的真实状态。四个视频素材,最后一个容量还很大,加起来大约有几十分钟,但噢措的汉语表达好像没有什么进步,讲的话加起来大约不会超过三分钟,而且还有不少重复。很显然,噢措的汉语口头表达,错过了一个孩子学习掌握母语之外一门语言的最佳时机。
令人欣慰的是,除了汉语口语之外,噢措门门成绩在班上都名列前茅。虽然在一群四年级的小学生中,她的身高远远超过同学们,但她已经不觉得难为情了。
有读者曾经问我,在《永远的四年级》中,噢措出场时,你写道:“小女孩拎着一个木桶,里面装满了水,水里倒映着一朵小小的云”。意象很美,但这是真的吗?
这当然不是真的,而是我的想象,但更是我的期望!
假如当年,早一点出现像月光妈妈这样温暖的云,噢措还会错过掌握汉语的最佳时机吗?
二 佛缘阁
2011年初秋的一天,月光对我说,她要去四川丹巴看望自己资助的那些贫困孩子,给他们捐赠一批图书和学习用品,问我有没有时间一起去?
月光的邀约,让我有机会踏上她的教育扶贫之路,近距离了解这位受藏地少年们爱戴的母亲,为什么会坚持不懈、年复一年地奔赴那片遥远的土地。
我们去的地方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巴底乡核桃坪,那是横断山脉褶皱深处一片古老的村落,也是大渡河上游大金川峡谷腹地中嘉绒藏寨的聚集地。
从地图上看,丹巴被山川和河流环抱着,白嘎山、四姑娘山、白菩萨山、小墨尔多山、墨尔多神山,海拔都在四五千米以上,四周的大金川河、小金川河、东谷河、革什扎河,像蓝色的缎带游走在山川,最终在丹巴汇入大渡河。
隐匿在横断山脉腹地中的丹巴藏寨民居
雪山上流淌下来的神水,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些河流,让它们永远也不会干涸。可是,也正因为雪山河流的层层阻隔,遏制了丹巴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多少年来,这块沉睡的土地,虽然景色如油画一般美丽,却依旧原始、蛮荒、落后、贫穷,像一颗珍珠,被蒙上了厚厚的污垢。
我们先坐飞机到成都,在一家客栈歇了一晚,然后从成都租了一辆结实厚重能开后门装货的全顺车,把随机托运来的十几箱图书和其他一些捐赠物资全部装上。由于东西太多,还拆掉了一排座位。月光说,我们这次走的线路,就是她2009年第一次来丹巴考察时的线路。先翻二郎山,到达泸定后,再走瓦丹路,沿着大渡河,一路奔丹巴。
她想让我体验一下赴丹巴的路。
进入大渡河峡谷后,感觉一路都在崇山峻岭的腰间爬行,一边是峭岩陡壁,不断有警示牌跃入眼帘:飞石路段,注意安全;滑坡路段,不要停留;垮塌路段,小心驾驶……另一边是瞅一眼就觉魂飞魄散的悬崖深谷,横亘河床的巨石时不时激起一堆堆水花四溅的白浪。每到山道拐弯处,我都会紧张得闭上眼睛,总觉得轮子一打滑,车子就会掉入深谷。
去往牧业村的路崎岖难行
提心吊胆中,我不由地想起自己小时候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那一首《四渡赤水出奇兵》中的歌词,我至今记忆犹新——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
这一路的难行,我是切切实实体会到了,只是我没有想到,当年红军闯过的天险之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路况的糟糕依旧没有什么改变。
我知道月光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免疫系统的疾病让她经常口腔溃疡,厉害时吃不下东西,所以体质也比较虚弱。面对杭州到丹巴这样遥远的距离和交通的艰难,我很难想象一个弱女子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下来的,她又为什么一定要越过千山万水,来到这样落后蛮荒的地方做教育扶贫?
等到了丹巴,走进核桃坪的那一刻,我心中的不解和疑惑,似乎瞬间就有了答案。
远远地,我们就看见耕读缘希望小学雪白的教学楼在艳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湛蓝的天空下高高飘扬,教学楼背后那一脉苍翠的山,学校屋顶上那蓬蓬勃勃的绿,伴随着清新的空气沁入心扉,一群穿着鲜艳藏袍的孩子手捧雪白的哈达,欢呼雀跃着向我们奔来。跑在最前面的几个漂亮的女孩子争先恐后地扑到月光怀里,其中一个长着柳叶般美丽眼睛的瘦小女孩,脸上笑靥如花,双眼却不停地流泪,她几乎整个人都黏在月光身上,那种毫不掩饰的依恋,就像女儿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母亲。
月光一边搂着这些女孩,一边逐个向我介绍:德吉拉姆、卓玛拉姆、拥忠斯姆,还有后面赶来的许方燕、杨英……
我这才了解到,月光不仅仅是在丹巴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她是把自己的心种在了丹巴。在2009年耕读缘希望小学落成剪彩仪式和开学典礼上,月光现场就认领了八个孩子,承诺每个孩子每年资助1200元学费和300元的物资,一直供到她们完成学业。
当年认识的这些孩子,几乎都出现在了《月光妈妈》书中,她们犹如开放在丹巴山野中雪白的梨花、粉红的桃花,灼灼放光。
德吉拉姆从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以后,已经成为一名白衣天使;卓玛拉姆在考上事业编进入政府机关后,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当作家的梦想;那个断臂女孩许方燕身残志坚,不仅以自己的实力进入上海驻成都的一家公司,业余时间还参加了马术队,在一次全国性的马术比赛中拿下金奖。
最让人吃惊的,是当年我第一次进丹巴时,一直黏在月光身上流眼泪的那个拥忠斯姆。2022年我专程去宜宾采访已经在那里工作的她时,她也是一直依偎在月光妈妈怀里,不说话,光流泪。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柔柔弱弱,从小失去父母关爱,有点自闭内向的小姑娘,居然有勇气辞去在一家公司的会计工作,在成都开了一家专门经营藏地首饰和工艺品的小店,她给小店取名“佛缘阁”,开业的那天还给我发来了现场的视频。
“耕读缘”希望小学落成暨开学典礼上的三个小花童(左起:拥忠斯姆、德吉拉姆、卓玛拉姆)
她在开业视频中播放的藏族名歌《一路有你》中唱道:一路走来,不离不弃,从此我不再孤单,因为有你,你是我命中的缘。
德吉拉姆对我说过,月光妈妈身上有一种佛性的光辉,很温暖,像妈妈一样。
而月光则毫不掩饰地告诉我,2020年她的事业陷入了低谷时,一度崩溃到想要自杀。先生就陪她来到丹巴散心,回到孩子们中间。当时,细心的德吉拉姆可能已经从月光的微信中感觉到了什么,见到后,一下抱住月光问:阿姨,你还好吗?虽然德吉拉姆什么也没有说,但她对月光妈妈的心疼和担忧却全都写在脸上。那一刻,一股暖流瞬间驱散了月光心中的抑郁和忧伤。回来以后,月光觉得自己就好了,她感觉丹巴对她的疗愈很神奇。
长大成人后的藏地姐妹花(左为卓玛拉姆,右为德吉拉姆)
假如把德吉拉姆的话和拥忠斯姆播放的歌联系起来,“佛缘阁”这个名字的由来,仿佛就不言而喻了。
三 寻找绿绒蒿
寻找绿绒蒿,可以说是我追踪采访旅途中最深刻的记忆。
小时候就知道雪域高原的藏红花是名贵的中药,却从未听说更珍稀的药材绿绒蒿。
当英措吉和德吉卓玛姐妹俩伴随着这两味中药材闯入我的笔下世界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寻找绿绒蒿。
英措吉后来告诉我,绿绒蒿被当地藏民称为“稀世之花”,这种只能生长在高海拔雪山顶上的“高原女神”,因寒冷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它一生只能开一次花,花开之时,就是绿绒蒿生命的绝唱;之后它就会耗尽自己所有的能量,结出无数颗小珠子一样的种子,然后静静死去。
英措吉的话,让我更坚定了自己必须去寻找绿绒蒿的决心。虽然我知道,雪山顶上、高海拔、花期极短,这一切都让你极难和开花的绿绒蒿相遇,但如果因为这一切而放弃寻找,我会不安,更会后悔。
为了见到绿绒蒿真容,我一次又一次艰难地登上雪山。山险路滑,高海拔带来的高反,都没能让我退缩。
我先后一共三次看到绿绒蒿,两次是黄色的绿绒蒿,一次是稀缺罕见的蓝色绿绒蒿。每一次和绿绒蒿的相见,心中都会涌上一种悲壮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亲历,无以言表。
《月光妈妈》书中《藏红花和绿绒蒿》这一篇,写得最为艰难。这种艰难不是文字的表达,而是文章背后艰辛的付出。因为我知道,假如我不是真正和绿绒蒿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亲手触摸它的花瓣,亲耳聆听它生命的绝唱,我无法写出书里今天呈现的对月光妈妈的深刻理解。
同样,在采写《仰望星空的牧羊女孩》宗吉的时候,我也很纠结是否要去草原深处寻找宗吉的妹妹吉毛。
宗吉是直亥村走出来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直亥草原上唯一一个攻读数学专业的藏族女孩。
有人说,数学是科学之王,能在数学领域里钻研的人,都是宝塔尖上的精灵。
然而,在采访宗吉的过程中我意外地了解到,这么优秀的女孩,居然有一个早早就辍学的妹妹。一奶同胞的两姐妹,父母亲给予的学习条件相信不会厚此薄彼,为什么一个能考上研究生,另一个却辍学生子,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径呢?
在青海师范大学开满海棠花和蒲公英的校园里,我见到了戴着棒球帽、穿着牛仔裤,青春逼人、英气勃发的宗吉。
想起第一次见到宗吉时,她家的母羊被山上的狼在屁股上咬了三个大洞,她搂着母羊伤心落泪的模样,而如今的宗吉,眼里有光,充满自信。
对于宗吉的优秀我已经充分了解,我更想知道的是,她的妹妹吉毛为什么会辍学?她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你作为姐姐,为什么当年没有劝阻妹妹?
树荫下,有两只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灰雀,一大一小,正围着一棵树皮在阳光下闪着银色光晕的白杨蹦跶。
宗吉专注地看着白杨树下两只蹦跳觅食的灰雀,眼神追逐着它们轻灵的身影。你能感觉到,这两只相依相伴的灰雀,牵动了宗吉的某种思绪。
好一阵,宗吉才回过神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有点恍惚地对我说:
不好意思,我想起小时候和吉毛一起抓小鸟玩的时候了。
停顿了一会儿,宗吉又说:这会儿,吉毛可能正在山上放羊。再过一两个月,到了夏季,她就要上山挖虫草了。
宗吉的这番话,让我下决心去寻找吉毛,亲眼看一看她现在的生活。
见到吉毛的时候,吉毛带着一个黑色的大口罩,只露出一双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古兰丹姆一样惶惶不安的眼睛,背上背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宗吉判若两人。
年纪轻轻的吉毛,已经是个单亲妈妈,带着年幼的儿子住在爸爸妈妈家。孩子父亲是谁?无人知晓,就像娘儿俩生命中飘过的一朵云,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仿佛是这个家里从未出现的过客。
我想问,但不知道怎么问。我终于明白月光说的:不敢问、不好问、怎么问?
一直陪同我寻访的月光,这时开了口:
我在直亥做公益这么多年,与孩子们交流时,最需要问的是父母的情况,但最不敢问的也是父母的情况,因为问着问着,心就疼起来,甚至不忍面对孩子们无奈和伤感的目光……
我们来这里建希望小学,并结对资助一批又一批孩子以来,公益团队的妈妈们每年都来看望自己结对的孩子,一对一地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心灵交流。十几年来,我们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我们也看到了直亥村教育的变化,更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月光妈妈和直亥雪山脚下的孩子们
此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显然,吉毛过早地被当地的旧习俗所困,以致早早辍学,这让她本来可以拥有多种可能性的人生旅途变得狭窄,一座大山就挡住她的视野,一片草原就阻断她的脚步!
而宗吉受了高等教育,读了研究生,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十分清晰。如今,她正朝着未来做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的方向努力。
同是一个家庭出来的两姐妹,吉毛留在了原地,背着孩子继续在草原放羊;宗吉却勤奋读书,开始仰望星空。人生的路径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一刻,我意识到:月光漫长而温暖的教育扶贫之路,不仅仅是捐钱捐物,更是用爱心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用微光照亮藏地少年的人生!(责编:孙小宁)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袁敏网上配资平台排名
发布于:北京市Powered by 炒股股票配资平台_线上炒股配资门户_怎么线上配资 @2013-2022 RSS地图 HTML地图